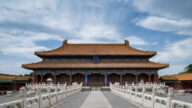【新唐人2009年9月2日讯】杜甫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不仅仅在诗作中嗟叹“国将不国”,更是立下雄心壮志,为复兴国家尽力。
如果说“诗史”的称号是从杜甫作品的历史价值角度来评价的话,那“诗圣”则是一个较为全面的评价,这个评价在诗界是至高无上的。正式把杜甫称做“诗圣”的,最早见于明代前期的陈献章。不过若论把杜甫尊为诗中圣人的观点,则早在唐宋间就有了。
首先对杜甫创作进行全面的评价并推许为最高地位的是唐代的元稹;他在为杜甫所写的墓志铭中曾道:“…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在这方面又推进一步的是宋代的秦观。他在《韩愈论》中把杜甫和孔子相比:“…杜子美之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其时而已。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集大成”是古代儒家评价孔子对我国过带文化所作的总结整理之功的赞语,这是所谓的圣人的事业。秦观虽然还没称孔子为诗圣,但已把杜甫比为诗坛上的集大成者了。
杜甫是个爱国的人。“爱国”与“忧国”显然不同。杜甫生活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转入衰败的关键时期。安史之乱造成之后百年的大动荡,国家屡屡被推向破亡的风头浪尖,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爱国诗人,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但杜甫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不仅仅在诗作中嗟叹“国将不国”,发出些呻吟,更是立下雄心壮志,渴望驰骋疆场,为复兴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他借戍边将士之口说“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骐驎,战骨当速朽”“男儿死无时”(《前出塞九首》)他向他的朋友大声疾呼,希望他们能同自己一起“济时肯杀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
他更勉励即将奔赴沙场的朋友“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寄董卿嘉荣十韵》)。杜甫这些充满爱国热情的诗歌对后世起到了巨大激励作用。在以后的时间里,每当中华民族遭受危难的的时候,杜甫的诗歌就会成为全民族的精神食粮。北宋即将亡国的时候,爱国名将宗泽因为朝廷掣肘,没有机会渡过黄河去抵抗金兵,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的诗句。
指挥中国历史上那场惊心动魄的“东京保卫战”的李纲,在敌军围城的紧要关头,亲笔题写杜诗分赠亲友,以表示自己誓与城亡的决心。最著名的例子是文天祥。他在被蒙古人抓到燕京之后,在监狱里关了三年。三年中,他始终不屈,坚持着民族气节,最后从容就义。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他在《正气歌》中说,“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本书,首先就是一部杜诗。
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二百首《集杜诗》,把杜甫的原句重新组合成一首首五言绝句,以此作为自己民族气节的一个核心内涵。甚至到了现代,当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成都时,许多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杜甫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诗句,最能表达当时人们的心情。
杜甫是一个非常重视修身养性的人。他一生得到的追求就是成为一个“儒”。他被人们称为“诗圣”,这个概念是宋代人首先提出来的,认为他是个“集大成者”。任何一个传统文人都清楚这四个字代表什么,因为这是孟子对孔子的称呼。孟子说,“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这个称谓可非同一般。
但是,杜甫一生都没有奢求自己能成为什么“圣”,他一生为之自豪的是自己的儒生身份。有人作过统计,他的诗歌中“儒”字共出现过45次,除了一次是指“侏儒”以外,其余44次都是指“儒家”。他自称“儒”、“老儒”(“干戈送老儒”,《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甚至用从来都是讽刺意味的“腐儒”二字自况。
我们不能否认他的一生中曾经有过对儒家思想的动摇,因为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曾说“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同山中一位儒生朋友一起嗟叹自己的怀抱没有机会实现。但是,杜甫最可贵的就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改变自己思想的核心。直到临终前在洞庭湖上漂荡时,他仍然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天地一腐儒”。综合他的一生来看,他真正符合孔子“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的要求。
杜甫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人。他不像李白那样看到政坛的黑暗便云游天下不再过问政事。他在各地漂泊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能得到为君王效力的机会。他早年自称“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话说得颇有些骄傲意味。就是这样一个踌躇滿志的人,却是一生不得意,最终落得“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成、华两县诸子》)的下场。
但是,他的“入世”,更多的是表现在他以平民的身份,以自己的道德为榜样去影响其他人。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类型,唯有杜甫以“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的平民身份出现在那张长长的名单上。在这一点看来,杜甫更像被孔子盛赞的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换个角度看,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坚持自己的理想并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杜甫,甚至比屡屡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这样牢骚的孔子更胜一筹。儒家向来宣扬“内生外王”的思想,认为好的政治家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就是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只要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就称得上“圣人”。
孟子本来就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发展到王阳明时代此话已经演变成了“满街都是圣人”,因为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达到道德高尚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失去了本色。这样看来,杜甫这样的人在世界上能够存在实在是难能可贵,因此,他能被称为“诗圣”。这个“圣”字更注重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