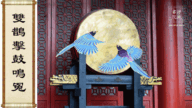13 歲時,李曼離開家鄉到了萬縣的柏土壩,1951土改時他21歲,在柏土壩教書,當過教導主任,訓育主任等等。
因為李曼出生地主家庭,土改時不准他留在學校,要他回家鄉接受清算,他只得回到洋沱壩(當時叫橫石村)。
按說李曼的父親因為抽大煙,已經破產,家中無田無地,壓根就不是什麼地主,可土改中李曼卻被評為了地主。
地主地主,顧名思義,指的是家裡有地的人。李曼家沒田沒地,怎麼會被評為地主呢?
李曼說,「滿了18 歲就要評地主,他們說我解放前在教書,沒有勞動,是剝削。當時有個說法叫『說理鬥爭劃地主,互相評地劃農民。』我回來後自己耕種那點土地,算不上什麼地主,問題出在農會追『浮財』。他們說我家裡藏有 3000斤黃金,於是我被抓到村上關起來,天天拷打,追逼金銀。」
李曼哪交得出來3000斤黃金?別說3000斤,3 兩他都沒有。可土改工作隊的人說:「金子銀子!你是個地主,怎麼會沒得金銀?要拿出來!」
交不出來,那就用刑。在被關押的幾個月裡,李曼遭受了幾十種不同刑法的折磨。
有一種刑法叫「蘇秦背劍」。什麼是「蘇秦背劍」?就是一隻手從肩上扭下去,一隻手從腰下扯上來,還把手扭翻過來,這個手這麼扭,這個手這樣扭,扭過來後把兩個手使勁一拉,用繩子把幾根手指捆在一起。這種刑罰在李曼身上用了幾十次。一捆就是幾個小時。「那幾個小時硬是受不了。」 李曼說。
還有一種刑法叫「飛機下蛋」。就是把人捆在五根板凳中搖晃。手放在下面捆起,腳放在上面捆起,捆好後搖晃板凳,板凳是活動的,把人一搖,扯得人所有骨頭要散架。儘管它整不死人,但能讓受刑者痛得過火。這種刑罰李曼也受了好多次。
「背磚」也是李曼受過的一種刑法。它先是把人面朝下睡在板凳上,手扭到背後把一雙大拇指捆在一起,再把兩個腳的大拇指用麻繩捆得緊緊的,然後把板凳豎立起來,把捆手和腳的繩子從板凳頭上掛下來,捆在板凳腳上。這一掛就受不了,人有那麼重呀。這還不說,他還在背心上加磚,一塊一塊的加。「我曾經被加過12 塊磚!我的媽呀,受不了。這種刑受一次後兩三天都吃不下飯。」李曼說。
再有一種刑法叫「猴兒扳樁」。就是用麻繩把兩個大拇指捆在一根木椿上,木樁上破一條縫,加一個木楔子,再用錘子砸木楔,當場把指頭整斷了的都有。幸虧當地婦聯主任同情李曼,把一根陳腐的麻繩交給行刑的民兵,捆上後,捶了幾捶,麻繩就斷了,再捆,「背磚」,再錘,又斷。所以這一關他躲過去了。
土改時的幾十種刑罰李曼都熬過去了,但最後有一種刑法卻差點讓他送了命。
「我永遠記得那一天——我22歲的生日。」李曼說。
他們把他脫光,手和腳反捆在一根棒棒上,再用一根麻繩把他生殖器捆起。棒棒就當作一把秤的秤稈,生殖器就作為秤鎬(秤稈上提稈的鐵環)。另外,在腳那一頭還掛一塊石頭,做為秤砣。捆他生殖器的麻繩上再接上棕繩,然後吊在樹上。他全身加石頭的重量就吊在他的生殖器上。就這樣,李曼肚子裡面的隔膜都被扯爛了,肚子裡的血從肚臍眼直往上噴,不知道流了多少血。
眼看李曼性命不保,在場的農會主任動了惻隱之心。他說:「這是個才出林的筍子呀(即:一個年輕人呀),不應該把他搞死了。」他一手托住李曼的身子,一刀割斷了繩子,把他救下來後,送到一個80多歲的老醫生那兒。最後,李曼的性命總算保住了,但促使生殖器勃起的附睪卻被扯爛了,「從22 歲我生日那天起,我就『殘廢』了,所以現在我是一個『淨人』(沒有生殖能力的人)。」 李曼控訴道。
講完這段不堪回首的經歷,李曼精疲力盡,癱倒在椅子上。
這還沒完。到了文革,李曼又被抓出來挨整。整人的人問他:「你怎麼沒死呢?」李曼說:「我當時想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就這麼一句話,差點又讓他送了命。整人者說:「你留得青山在,你是還想來造反吶?」一頓暴打!李曼被打得昏死過去,躺在地上沒有知覺了。這時,整人者又唆使村裡兩個人來整他。他們一個拿一把柏樹皮,捆成很粗的火把,來燒李曼的眼睛。「他們說我土改時沒有整死,文革中就要把我打死。我眼睛當時是燒瞎了,什麼都看不見了。我在地壩上躺了一夜,天要亮時才有兩個人把我拖回去。」
和李曼住一個院子的一個人同情他,請了李曼的學生青龍口醫院的院長羅遠明,和李曼的同班同學大水井的眼科醫生冉玉清來救他。結果李曼人是被救活,眼睛也保住了,但從此只能辨清一、兩尺內的人和物。(根據譚松《血染的土地》整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