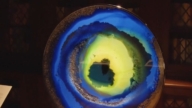【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9月14日訊】燦爛輝煌的文藝復興可謂是西方藝術史上最為重要的一個時期了,其影響之深遠,猶如歷史篇章裡的黃鐘大呂,震古爍今。本次人類文明中的美術在文藝復興時期走向成熟,並對其後兩百年的西方藝術有著直接的影響。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文藝復興之後的兩百年卻是各類相生相剋因素處於激烈而又微妙的衝突下,陰陽平衡被逐步打破的階段,所涉及因素之龐雜、其背後範圍之深遠,絕非筆者一兩篇文章所能講得清楚的。因此,本文只是根據個人粗淺的理解,從幾個方面簡單地談一談當時西方美術的大致情況,以及這段歷史帶給人的一些啟示。
美術發展的日漸式微
科學與思想的變革對美術的影響是巨大的。最明顯的現象就是宗教主題作品在比例上呈逐步減少的趨勢,包括在鼓勵宗教題材創作的天主教國家裡也是如此。進入十八世紀後,這一趨勢在整個歐洲可謂愈演愈烈。
這種情況的出現其實也在常理之中。如果一個畫家不信神或者不怎麼信神了,那麼他的創作重心自然不會放在如何表現神那裡。除非有這方面的訂單,否則畫家在個人的創作中就不會去畫神;而當有訂單時,不信神的畫家則是以牟利為目的去畫神,畫面上不自覺流露出來的心境,與所要求的那種真正虔誠信仰的意境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別,作品所帶的信息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在十八世紀承襲巴洛克風格的洛可可時期,美術呈現出向兩方面發展。在宗教作品中,藝術家們一如既往地表達天國的神聖與輝煌,在藝術形式上除了繼承此前巴洛克風格的活躍動勢、恢宏風貌外,更加側重於技藝手法的輕盈靈巧與裝飾元素的豐富纖細等因素。而在世俗藝術中更多描繪的則是人世的浮華與情感的細膩浪漫。此時的世俗主題多表現上流社會快樂生活、追求情愛等內容,或以神話題材來作隱喻,表達生活的樂趣。

人間的藝術自然可以表達世俗生活,這本是沒有問題的。但此時的世俗藝術在去掉神聖因素後形成了一種趨勢,變得越來越低俗,那就成問題了。從藝術史中可以看到,十八世紀中、後期的一些知名畫作已經放棄了以前借用神話來掩飾的遮羞布,直接去表達違背道德的主題了,比如表現同時代男女偷情的場景,甚至描繪一些猥褻的畫面等。但那時敗壞了的社會風氣卻讓某些色情畫家在美術界身居高位,頗負盛名。
從藝術水平上看,洛可可式的室內裝潢和家具造型等實用藝術始終具有非凡的美感與不朽的工藝價值,這與今天的美術史書上所常見的洛可可「代表畫家」們在創作題材方面的低俗顯得格格不入。事實上,人們還是能夠找出一些立意優秀的洛可可作品的,但由於啟蒙主義等變異的思想熱衷於宣揚追求自由、反對傳統禮教束縛的觀念,加之社會高層的享樂與腐敗,導致那些破壞道德的作品卻被吹捧了起來,造成了藝術迅速走向敗壞的惡果。
歷史的發展始終都遵循一定的規律,即使在多重相生相剋的制衡作用下,此時的陰陽卻在一點一點地滑向失衡——陰越來越強盛,而陽則在削弱。雖然洛可可藝術也屬於正統藝術之一,但也是傳統發展到後期陰盛陽衰的體現。洛可可風格的藝術品位講究往細小處走,著眼於細膩、瑣碎的裝飾風格,不再有前代藝術的大氣與雄渾。受這種藝術的影響,男性行事風格也逐漸像女性般優雅。上個世紀的美國歷史學家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在他的書中對此評價道:「這個時期的藝術缺乏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藝術作品中公認的男性氣概和力量特徵,它是女性藝術而非男性藝術。從男人的服飾、家具,還有他們一邊用漂亮的中國茶具喝著巧克力奶,一邊津津樂道地談論著政治上的流言蜚語,就能斷定洛可可時期是女性時期而不是男性時期。」
如果說這種變化還在能接受的範圍之內,那麼法國大革命後,更嚴重的變異便無法讓人接受了,那些東西將取代正常的陰陽,魔鬼開始一步步統治世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藝術的敗壞並不僅僅局限於作品的立意。由於意識和物質是一性的,所以當整體藝術思想出現問題的時候,作為承載其藝術思想的物質媒介本身同樣會出問題。這一點也是唯物主義者們所想像不到的。
科學的發展,使畫家們得到了材料成本更為低廉、價格更為便宜的顏料。原來需要從某些貴重的天然礦物中提取的色料,隨著科技的進步,通過化學的方式就能從廉價的材料中合成。
以群青(Ultramarine)為例,傳統的群青色由於來源於稀有礦石青金岩(Lapis lazuli),所以極其昂貴,高品質的青金石甚至超過了黃金的價格。這種以寶石為原料所製成的藍色顯得異常高貴、飽滿、莊嚴,色澤璀璨。而虔誠的古人認為應該用最珍貴的顏料來讚頌神,因此,傳統繪畫中聖瑪利亞(Saint Mary)的衣服就一直是群青色的。
十八世紀初,當人們以近代化學的方式合成出價格更為便宜的普藍(Prussian blue)顏料後,不少畫家認為其近似的色彩能作為昂貴群青色的替代品,並在創作中付諸實踐——至於神聖與否,那早已不在此時人們考慮的範圍之內了。但是化學合成的產物如何能與真正的天然寶石同日而語?普藍顏料無論在純度、亮度、耐久度、耐光性等諸多方面都遠不及真群青,即使到了科技發達的今天,這些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完美解決。尤其在化學還不發達的階段,因此而造成油畫的變色、發黑、開裂等各種麻煩隨著時間的流逝層出不窮。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一些其他顏料上,這裡就不一一贅述了。
有關繪畫材料的改變還涉及到調色油的變化。歷史上原本用於主流油畫媒介中的乾性油類是亞麻仁油(Linseed oil)與核桃油(Walnut oil),這兩種乾性油在空氣中氧化後的結膜非常堅固,很適合於製作油畫顏料。但油類在繪畫上都有一個缺點,就是會隨著時間慢慢變黃。因此,一直有不少畫家試圖找到不會變黃的油。十七、十八世紀後,荷蘭、法國和意大利的畫家們越來越多地採用罌粟籽油(Poppyseed oil)來製作顏料,因為這種油變黃的幅度小於其他油類。
罌粟籽油在繪畫上的運用並不算某種發明,因為人們很早以前就已經了解這種油的特性了。但罌粟這種植物在文化上的象徵意義卻讓人敬而遠之,因為它在西方文化裡一直是睡眠與死亡的象徵。在古希臘和古羅馬神話中,罌粟曾被視為獻給死者的禮物。可想而知,這種不吉利的植物在相信鬼神的年代裡會有多麼受排斥。然而到了經過啟蒙運動洗腦的時代,科學化的思想讓人們更願意從實用角度出發,並將那些古代文化束之高閣。
其實不止西方如此,東方也同樣有類似的文化。中國清代的《右台仙館筆記》中闡述諸神以「鴉片煙劫」來清理道德敗壞的人類時,也曾提到罌粟內被灌注了無間地獄中罪魂的膏血。此書在卷二寫道:「然罌粟本屬草花,自古有之,其汁淡薄,不能熬膏。故又命九幽主者,於無間地獄中,擇取不忠、不孝、無禮義廉恥諸罪魂,錄送此間,榨取膏血,轉付地上山陵原隰墳衍之神。使將此膏血灌入罌粟花根內,自根而上達花苞,則其汁自然濃郁,一經熬煉,光色黝然。」
對鬼神之說嗤之以鼻的實證科學讓人迷信於親眼所見的事物,但人的眼睛卻有相當大的局限,看不見的東西太多,而且只看到眼前與表面勢必會造成短視。從短期來看,罌粟籽油的確非常清亮透明,色澤很淺,但隨著油膜的老化,多年後它與亞麻仁油的變黃狀況其實沒有多大區別。然而從結膜的堅固程度上講,亞麻仁油明顯要比罌粟籽油優秀很多。同時,罌粟籽油乾燥非常緩慢的特性,始終讓色層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在傳統的多層畫法中,如果下層使用了罌粟籽油,就必須等待很多天,直到它乾透後才能再畫新的色層。但實際作畫時,一般是沒有那麼多時間待乾的。而當底層還沒有徹底乾燥就畫上新的色層後,便會造成開裂。
這些負面情況出現的頻率非常高,以至於美術史上幾代材料學家,從十八世紀出生的蒙塔貝爾(Jacques-Nicolas Paillot de Montabert,1771年 – 1849年)到十九世紀的愛伯奈爾(Friedrich Eibner,1825年 – 1877年),再到二十世紀的多奈爾(Max Doerner,1870年 – 1939年),都對罌粟籽油頗有微詞。愛伯奈爾甚至直言這種油完全不適用於油畫。但圈內的人都知道,罌粟籽油一直在被廣泛使用。為什麼?因為很多生產管裝顏料的廠家喜歡不易乾的油,這樣,商品在沒賣出去之前就能儲存得更久;而且,顏料擠出來後,不泛黃的透明油感能讓商品的成色顯得更好看,自然能吸引買家。
可見,科學是發展了,但美術卻在走向衰敗。現代人發明了各種高級的顏料,卻很難再看到凡·艾克(Jan van Eyck,約1390年 – 1441年)時代的作品中那種明亮、清麗、優美的色彩了。科學不發達時代的油畫可以保存六百年;而到了科學發達的今天,如果一幅油畫在五十年內不出問題,人們就可以稱讚顏料的質量了。眾所周知,所謂「先進」的科技時代從來也沒有造就出一位能比肩文藝復興大師那樣的藝術巨匠來。科學的進步只是表面的浮光掠影,而道德的下滑卻造成了人類所遇到的種種困難。
(待續)
(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