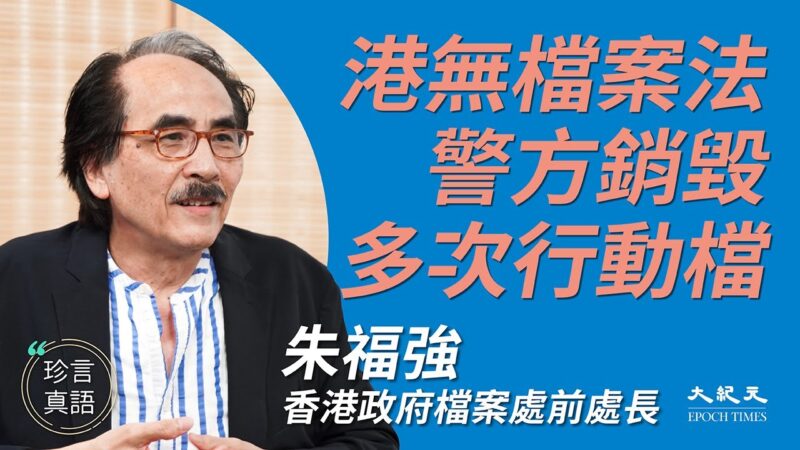【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5月21日訊】「檔案就是證據,是提供將來發生同類事件時的參考,也是民主社會問責的依據。」香港前檔案處處長朱福強,是近年積極參與「檔案法」立法的倡議者,他接受《珍言真語》專訪時說:「如果沒有檔案,說難聽一點,政府是可以無法無天的。」
今年4月初,香港行政署答覆立法會查詢時表示,2015至2019年間「未經授權銷毀非機密業務案卷」數目及有關內容共2,925個,其中警務處占94%,因而受質疑警方在2014年雨傘運動及2016年旺角事件中,濫捕的證據已被毀屍滅跡。也令外界憂心反送中運動中警察濫捕、暴力執法的證據也將難以保存。
「警察回答立法會的問題,說銷毀了很多行動的檔案,但是,你不知道是什麼檔案。銷毀了很重要的檔案、證據,我們都不知道。」朱福強說。
「我常常告訴學生,要求真相,一定要找檔案。」身兼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座副教授的朱福強說,檔案在公事過程中產生,記錄下公事的真相,「雖然有人在事後改檔案,但檔案即使改了,也能表現出是改過檔案的,因為這是事實。」
疫情當前,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顧問的朱福強說,近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檔案理事會」等國際文獻組織聯合發表聲明,呼籲保存疫情所有相關文件與數據,「尤其是政府重要的決定、重要的事項記錄,要記錄下來。」
「這個時期政府做多少事,它決定封不封關、決定那個社區隔離,這些影響到多少人的生活,多少人的生意。」他強調,留下具參考價值的紀錄,可助於人們避開將來可能發生的更大災難,「而且還有問責,誰決定這件事?要做這件事不做那件事,影響是什麼?問責是相當重要的,民主社會裡什麼都要問責的。」
他強調即使因應疫情,公務員在家辦公,公事過程中產生的檔案也需歸檔,「這些記錄一定要正正確確地、專業地歸檔。」尤其電子化時代,以電郵代替信件與公文往來,「整個數字化,這些東西的管理、儲存,究竟有沒有人想過。」
「所以我們一定要推動檔案法,因為檔案法規定政府銷毀任何檔案,一定要得到檔案處處長的同意,如果不是,就犯法的。」「規定整個檔案處的架構、監察,和法律上規定政府怎樣去管理檔案,清清楚楚。」
檔案記錄事實,是真相,是民主社會裡人民追責的依據,推動檔案法即是保障檔案的保存,「如果沒有檔案,政府是可以無法無天的,因為沒有證據,我(政府)怕什麼呢?人民的很多權益就無法保障。」朱福強表示,日漸殆失民主、法治的香港,檔案法尤為重要。
此外,近期DSE歷史科試題爭議風波,香港學術界瀰漫白色恐怖,朱福強並不因此噤聲,「不單單是學者,每一個人、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我知道檔案的事,一些的內幕,那我就說出來。」
「其他學者真的應該出來,他們不出來可能有很多個人的考慮,我不知道。但我始終覺得,每個人都走出來說話的時候,就會沒事的。」朱福強說。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楊潤雄假意裝睡 明知無錯但說錯
記者:前檔案處處長朱福強教授,也在中文大學任教歷史課系,請教對考評歷史學科爭議的看法?
朱福強:我在中大歷史系,嚴格來說我不是教歷史的,是教檔案學、檔案管理學、檔案欣賞、檔案利用等。這個問題本來應該由教歷史的大教授,他們來講更加適合,起碼比我更加適合,可惜到現在還沒有有頭有臉的人敢走出來講。
稍早劉細良(香港前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資深時事評論員)說,是否應該有人出來講一下,我覺得也是應該的。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我從普通常識去看,有幾點可以談談,第一究竟這個題目是否出錯了呢?如果沒有出錯,為什麼教育局楊局長說出錯了?那錯在哪裡呢?坊間有這麼多討論,都說沒有出錯。沒出錯為什麼楊局長堅持說出錯了呢?是否就像有人說的在裝睡,假裝不知道呢?明知道沒有錯的但說錯了。我不知道,這個可以談談,這背後有什麼動機呢?
考試題目是「中日關係在1900年至1945年,中日雙方的交往到底是否利多於弊?」他沒有說利多還是弊多,他提供的那兩份資料很明顯是有利的,這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說出錯了,我覺得在技術上出錯了。倒過來,如果是問「中日交往1900年至1945年是否弊多於利呢?」然後找兩份文件,說日本人把中國人打得狗血淋頭、中日戰爭等兩份文件,然後問同學你同意不同意,可能就沒人出聲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他可能就沒有意見。但你現在這樣問,是否在引導他們呢?所以之後有人在討論、辯駁,沒理由是引導,這是個開放式的問題,只是問你同不同意,你可以說不同意也可說同意,倒過來問弊多於利也是一樣的,所以你問我是否出錯了,我說這方面技術上被人抓住了。
有消息說這個題目教育局一早就知道了,如果是這樣,教育局是否有心搞陷阱讓人踩下去?然後借題發揮,很多人這樣說,這個很有意思。但是我相信楊局長他一定會知道1900年至1945年這段時間中日之間的交往,一定是有利有弊。當然弊的地方就是中日戰爭,這不用說了,什麼7.31那時已經開始打仗了,接著南京大屠殺,一直往南方,直到炸重慶,中國人民是很慘的。
但在之前,中日有很多交往,我不相信他不知道,我覺得他是故意不說的,中日之間那種交往,尤其是中國派遣留學生到日本。一直以來日本的明治維新,向西方學習、強國,中國戰敗輸給日本,想向西方學習,但在中國戰敗之前,1872年,中國已經派留學生去海外留學,早期有詹天佑,後來就多些去日本,大概在清末的時候去日本,原因很簡單日本近又便宜,這方面日本對中國現代化發展是有利的,不要說毛澤東的言論了,說日本打中國便利共產黨壯大,這個先不說,但事實上交往對中國是有利的。當時去日本的留學生有蔣介石、魯迅,郭沫若、秋瑾、李大釗,但看回當時中國派這些學童或年輕人留學,是有個研究pattern(模式)的,派遣到歐美國家的,比如去英國像嚴復等人,去美國的詹天佑,詹天佑回來就是鐵路之父。去西歐留學的那些,基本上是學科技、科學這些,但去日本留學的,個個都是很激進的,你看蔣介石、秋瑾。
記者:走民主之路的。
朱福強:沒錯,我看過一個研究說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因為日本是軍國主義militarism,nationalism(民族主義)等等,去日本留學的留學生他們接近中國,中國發生什麼事他們是很近看到的,像嚴復、胡適那些人去到大西洋那邊,(中國)發生什麼事情也不知道,可能他們可以安心的研究學問,是理性一些。這班人又不是理性一些是感性一些的,所以這些是可以討論的,楊局長說什麼沒有討論空間,如果我在大學裡教學,對學生說沒有討論空間,我就會被人解僱了。
記者:林鄭說這個不是政治干預教育。覺得現在政府所做的事是不是政治干預教育呢?
朱福強:我想她不用做任何事,她說一句話也是干預了,因為她有公權力,她是特首,她說一句話下邊那些人都會做的,她為什麼不是干預呢?
記者:現在說考評局不是獨立於教育局,因為她沒有這個權力所以需要她過問一下都是應該的。
朱福強:到今天老實說如果還有法治的話,還有這麼清清楚楚的話,我們就不用那麼擔心了。你說考評局是獨立的,你廉政公署也是獨立的,很多都是獨立的,醫館局也是獨立的,實際上是怎樣呢?大家都心裡有數。
教科文薦紀錄政府重要決定和事項 民主社會需問責
記者:另一個話題檔案法,說說你的見解。
朱福強:我很關注這件事情,在國際上已經有一個聯合的聲明,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檔案理事會」國際那些文獻組織、很多國際的組織是聯合發表了一個聲明,就是要大家在這個疫情當中千萬不要忘記將一些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政府重要的決定、重要的事項記錄好記錄下來。想想在這個時期政府做多少事,它決定封不封關、決定那個社區隔離(social distancing)這些影響到多少人的生活,多少人的生意,這麼重要的事情我們一定要記錄下來,就是後面一定有記錄,這不只是將來同類型事情發生的時候,這個記錄給了我們很大的參考價值,幫我們避開將來可能更大的災難,而且還有問責,誰決定這件事?要做這件事不做那件事,那個影響是什麼?問責是相當重要的,民主的社會裡什麼都要問責的。
記者:但政府可以說可以停擺的幾個月,很多工作都可以⋯⋯
朱福強:什麼叫做停擺呀?你(港府)以為整個世界像電燈那樣隨便關掉嗎?公務員仍然在家裡工作(Working from home),這裡也有一個問題:公務員在家裡工作的話,我經常跟學生講:檔案是什麼來呢?檔案就是任何公事過程中會產生的任何記錄,這些記錄一定要正正確確地、專業地去歸檔,沒有歸檔就會很亂,一定要歸檔,這就叫做檔案。在家裡工作的公務員,他們在公事過程當中,我真是很想問:你們這一幫人有沒有歸檔啊?
記者:是的,我們以後可以查看文件。
朱福強:是的,尤其是現在的文件,再不是以前那樣,我寫信給你,你寫信給我,有白紙黑字,不是這樣的了,都是數碼,整個digitization(數字化),整個digital(數字)一個這樣的世界,電郵全部都不是摸得到。我的意思就是說,這些東西的管理、儲存,究竟有沒有人想過。
警方銷毀多次行動檔案 行政指令架空檔案管理
記者:你對於檔案是特別看重,早些時候見到有報告,警方銷毀了一些檔案,那些情況是怎樣的?
朱福強:就是每一年,立法會的議員,他們幫本土研究社,因為他們是做一些這樣的檔案,做這些叫做問責這樣的議題,他們每一年都問,尤其是在財委會會問那些部門,檔案管理的情況,特別是銷毀了些什麼?銷毀了多少?那次警方的回答,「銷毀了很多行動的檔案」,但是,它沒有講是什麼檔案,但是,在那段時間裡,有「反送中」,接著有「佔中」,那些檔案銷毀了,老實說,現在的情況是沒有檔案法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推動檔案法,因為檔案法規定政府,銷毀任何檔案,一定要得到檔案處的處長的同意,如果不是,就犯法的。但現在檔案處的處長最麻煩的地方,就不是一個專業的職系,他是普通一般的職系,你問檔案處的處長銷毀不銷毀?他們不夠膽說不銷毀的,他是不是想不幹了?是不是?所有為什麼我們說檔案法裡,規定整個檔案處的架構、監察,和法律上規定政府怎樣去管理檔案,清清楚楚,現在沒有,只不過是行政的指令,所以剛剛問的問題就是,這個警察回答立法會的問題,銷毀了多少,但是,都沒有辦法,你不知道是什麼來的,銷毀了很重要的檔案,很重要的證據,我們都不知道。
政府一要產生檔案 二要保留好紙本和數碼檔案
記者:是啊,我們一直講獨立調查,如果燒了一些檔案,以後獨立調查怎樣去找回證據?
朱福強:沒有錯,任何調查都好,都一定需要檔案,我們講檔案就是證據,不留下證據怎樣去調查呢?所以我會覺得,在現在這個時代,這麼激盪,又有疫情,大家都不要忘記,因為檔案是涵蓋一切,政府做任何事都產生檔案,你就要告訴政府,第一,你一定要產生檔案,你不要「側側膊」矇混過關;第二,產生了之後,一定要好好的保留,不論這個檔案是紙張也好,數碼檔案,電郵也好,什麼都好,尤其是電郵檔案,是一個最難管理的一個檔案的種類。
記者:感覺上檔案,會像一些機密,香港和大陸這麼接近,可能某些檔案中國是很有興趣想知道的。
朱福強:有,政府裡通常一件公事,決定這件公事的,那個叫做保安程度,所以政府裡面有分別的,譬如,一般的公事,他們叫做普通檔案,中文叫普通,英文叫做General普通檔案,那些咖啡色封面的那些檔案。如果公事是機密一點,機密公事產生機密檔案,絕密公事產生絕密檔案。它認為機密一點的,它就會把那些檔案,叫做Classify(分級別),把它變成,譬如是Confidential機密,或者叫Secret絕密,或者叫Top Secret高度絕密,它是這樣分別的。
不過是這樣,請記住,不管檔案是什麼等級的保安分類,它都是檔案,它都是公共檔案,都是我們給錢給它(政府)產生的,因為他們(政府人員)的工資是我們發的,那些紙張是我們買的,電腦是我們給的。所以產生的檔案是公共財物,是應該受檔案法來規管的。無論是怎樣的機密都好,最多是說非常機密的那些,可以的,那你就不要開放吧,美國也是這樣的,英國也是一樣的。
若香港無檔案法 政府無問責民主缺失
記者:是,但香港如果沒有檔案法的話,會帶來什麼樣的損失呢?
朱福強:那就大了。首先在民主社會裡,在香港沒有民主啦,但最低限度如果有檔案法的話,政府對於任何的公事產生檔案,將來我們有什麼事情問責,它是問責的基礎,如果沒有檔案,難聽一點說政府是可以無法無天的,因為沒有證據,那沒有證據他怕什麼呢,於是人民的很多權益就無法保障,有很多這樣的例子的。譬如我隨便舉一兩個例子吧,以前的愉景灣,改換了地權,之前愉景灣全部都是矮屋,突然之間一下子有很多高樓大廈,那個發展商好像是興業,那它應該要補地價的嘛,但是它沒有補。
記者: 他們和梁振英的關係好啊。
朱福強:總之他們沒有補到。後來立法會去查,當年的損失是16億,不知是70年代末還是80年代初。那我就問你啦,那錢去了哪裡呢?後來政府查問,是誰做的,沒有補地價,但是都沒有人理。立法會有一個查詢,但是不了了之,那些官員說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那時候(前政務司司長)鍾日傑都有上去說,「我不知道啊。」土地lands department那個處長也說,「我也不知道啊,我的同事找不到檔案啊。」可以一兩句話就完全沒有關係了。
記者:香港現在充滿了謊言的時代,檔案作為歷史的見證的作用性?
朱福強:是啊,謊言嘛。檔案,我常常和學生講課的時候,我說你要求真啊,一定要找檔案,truth,檔案是在公事過程中產生,產生的時候沒有想到要做假,你要知道那個公事的真相,就要找回那個公事的檔案。雖然也有些例子有人在事後去改檔案,那個檔案本身即使改了也能表現出是改過檔案的,因為這個是事實。舉個例子當年唐英年,那個盧維思(Michael Rowse)申請司法覆核,被別人硬要燉他冬菇(降級),要他承擔那個SARS「維港匯」事故的失敗責任,唐英年改了那個會議記錄。
記者:無論做了什麼事情都會被記錄下來,但「8.31」我們現在還看不到任何的文件。
朱福強:是啊,沒有啊,如果那消息是報導正確的話,那地鐵公司是把那些影像消滅了,你也不知道的,所以就是要調查啊,要獨立調查。
每個香港人應站出來 都走出來就會沒事
記者:這一次能夠請到你來也是不容易,現在教育界受到很大的打壓,怎麼看香港的學者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朱福強:都是那一句話,每一個人,不單單是學者,每一個人、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我都只不過是站在我自己的崗位上,我知道那些檔案的事,一些的內幕,那我就說出來,我不是想要去煮(推波助瀾)批評這個政府,我說出來的是希望真的可以改善。其他學者他們真的應該出來的,他們不出來可能是有很多個人的考慮,我不知道。但是我始終覺得,你走出來說話,每個人都走出來說話的時候呢,就會沒事的。
觀看【珍言真語】系列視頻。
(轉自香港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