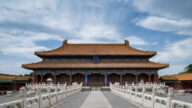【新唐人2009年9月2日訊】杜甫與其他人的最大區別在於,他不僅僅在詩作中嗟嘆“國將不國”,更是立下雄心壯志,為復興國家盡力。
如果說“詩史”的稱號是從杜甫作品的歷史價值角度來評價的話,那“詩聖”則是一個較為全面的評價,這個評價在詩界是至高無上的。正式把杜甫稱做“詩聖”的,最早見於明代前期的陳獻章。不過若論把杜甫尊為詩中聖人的觀點,則早在唐宋間就有了。
首先對杜甫創作進行全面的評價並推許為最高地位的是唐代的元稹;他在為杜甫所寫的墓志銘中曾道:“…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在這方面又推進一步的是宋代的秦觀。他在《韓愈論》中把杜甫和孔子相比:“…杜子美之與詩,實積眾家之長,適其時而已。
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集大成”是古代儒家評價孔子對我國過帶文化所作的總結整理之功的贊語,這是所謂的聖人的事業。秦觀雖然還沒稱孔子為詩聖,但已把杜甫比為詩壇上的集大成者了。
杜甫是個愛國的人。“愛國”與“憂國”顯然不同。杜甫生活的時代正是唐王朝由極盛轉入衰敗的關鍵時期。安史之亂造成之後百年的大動蕩,國家屢屢被推向破亡的風頭浪尖,因此這一時期涌現出了大量的愛國詩人,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但杜甫與其他人的最大區別在於,他不僅僅在詩作中嗟嘆“國將不國”,發出些呻吟,更是立下雄心壯志,渴望馳騁疆場,為復興國家盡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他借戍邊將士之口說“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騏驎,戰骨當速朽”“男兒死無時”(《前出塞九首》)他向他的朋友大聲疾呼,希望他們能同自己一起“濟時肯殺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他更勉勵即將奔赴沙場的朋友“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寄董卿嘉榮十韻》)。杜甫這些充滿愛國熱情的詩歌對後世起到了巨大激勵作用。在以後的時間里,每當中華民族遭受危難的的時候,杜甫的詩歌就會成為全民族的精神食糧。北宋即將亡國的時候,愛國名將宗澤因為朝廷掣肘,沒有機會渡過黃河去抵抗金兵,臨終時念念不忘的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蜀相》)的詩句。
指揮中國歷史上那場驚心動魄的“東京保衛戰”的李綱,在敵軍圍城的緊要關頭,親筆題寫杜詩分贈親友,以表示自己誓與城亡的決心。最著名的例子是文天祥。他在被蒙古人抓到燕京之後,在監獄里關了三年。三年中,他始終不屈,堅持著民族氣節,最後從容就義。是什麼東西支撐著他?他在《正氣歌》中說,“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這本書,首先就是一部杜詩。
文天祥在獄中寫下了二百首《集杜詩》,把杜甫的原句重新組合成一首首五言絕句,以此作為自己民族氣節的一個核心內涵。甚至到了現代,當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到重慶、成都時,許多因戰爭而背井離鄉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杜甫那首《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的詩句,最能表達當時人們的心情。
杜甫是一個非常重視修身養性的人。他一生得到的追求就是成為一個“儒”。他被人們稱為“詩聖”,這個概念是宋代人首先提出來的,認為他是個“集大成者”。任何一個傳統文人都清楚這四個字代表什麼,因為這是孟子對孔子的稱呼。孟子說,“聖人”是“人倫之至”(《孟子·離婁上》),這個稱謂可非同一般。
但是,杜甫一生都沒有奢求自己能成為什麼“聖”,他一生為之自豪的是自己的儒生身份。有人作過統計,他的詩歌中“儒”字共出現過45次,除了一次是指“侏儒”以外,其餘44次都是指“儒家”。他自稱“儒”、“老儒”(“乾戈送老儒”,《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甚至用從來都是諷刺意味的“腐儒”二字自況。
我們不能否認他的一生中曾經有過對儒家思想的動搖,因為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中曾說“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同山中一位儒生朋友一起嗟嘆自己的懷抱沒有機會實現。但是,杜甫最可貴的就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也沒有改變自己思想的核心。直到臨終前在洞庭湖上漂蕩時,他仍然可以自豪地稱自己是“天地一腐儒”。綜合他的一生來看,他真正符合孔子“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的要求。
杜甫是一個積極入世的人。他不像李白那樣看到政壇的黑暗便雲游天下不再過問政事。他在各地漂泊的過程中無時無刻不盼望著能得到為君王效力的機會。他早年自稱“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捲,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話說得頗有些驕傲意味。就是這樣一個躊躇滿志的人,卻是一生不得意,最終落得“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飢卧動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牆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投簡成、華兩縣諸子》)的下場。
但是,他的“入世”,更多的是表現在他以平民的身份,以自己的道德為榜樣去影響其他人。中國歷史上仁人志士不少,但大多數都是在國家危亡的時候“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類型,唯有杜甫以“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的平民身份出現在那張長長的名單上。在這一點看來,杜甫更像被孔子盛贊的顏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
換個角度看,無論在何種境遇下都堅持自己的理想並在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的杜甫,甚至比屢屢發出“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子罕》)這樣牢騷的孔子更勝一籌。儒家向來宣揚“內生外王”的思想,認為好的政治家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這就是所謂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普通人過平凡的一生,只要能實現道德人格的完善,就稱得上“聖人”。
孟子本來就承認“人皆可以為堯舜”,發展到王陽明時代此話已經演變成了“滿街都是聖人”,因為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達到道德高尚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在社會這個大染缸里,絕大多數人都已經失去了本色。這樣看來,杜甫這樣的人在世界上能夠存在實在是難能可貴,因此,他能被稱為“詩聖”。這個“聖”字更註重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水準。